一个字幕制作者的自白》,作者尼克-兰利
随着第 9 卷的出版,《世界哺乳动物手册》系列也将完成。 因此,现在是回过头来反思这项不朽工作背后的巨大努力的好时机……HMW 团队的一位成员最近就是这样做的,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 尼克-兰利(Nick Langley)撰写了整套丛书的绝大部分图片说明,仅在几卷中与其他人分担了工作。 考虑到 HMW 系列包含来自 1100 多位摄影师的 4582 张照片,这需要大量的说明……和大量的工作! 非常感谢尼克为该系列所做的重要贡献,感谢他与我们分享他深思熟虑、机智幽默的 “字幕组自白”,我们相信您会喜欢的!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的商业和技术记者,我的职业生涯漫长而富裕,但并不充实。
我庆幸地离开了电脑和管理术语的世界,在国际鸟盟担任编辑顾问,工作充实但收入微薄。 我撰写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新闻稿和报告,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减轻专职保护工作者的压力,使他们能够专注于真正工作的东西。 我对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有着终生的业余兴趣,但在鸟盟,我第一次被专业人士所包围。 我低着头,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学到了很多东西。
鸟类生命组织深入参与了 Lynx Edicion 的《世界鸟类手册》。 当何塞普-德尔-霍约(Josep del Hoyo)找到鸟类生命通讯主管阿德-朗(Ade Long),希望为《世界哺乳动物手册》的配套丛书寻找一名标题撰写人时,我很幸运地在那里工作。 我会永远感谢阿德把我的名字推荐给他。 他一举将我推到了新世纪最雄心勃勃、最成功的出版项目的核心位置。
我曾为当时的鸟类生活杂志《世界观鸟》撰写过何塞普的简介,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阿德的推荐,他邀请我为《世界观鸟》第一卷《食肉动物》撰写一些标题。
为了弥补我在工作上的明显不足,我的新闻背景为我提供了两个优势。 其一是用恰当的字数表达必要信息的能力。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经常担心被起诉,所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高。 我并不太担心心怀不满的哺乳动物会采取法律行动,但幸运的是,我养成了检查一切资料来源的习惯。
事实证明,在精确的字数内获取正确信息的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杂志或报纸的栏目不会留有空隙,但 HMW 和 HBW 的版式要求标题的长度有所变化。 我知道这一点,我也努力过,但我长期习惯于听从可怕的编辑和副主编的指令。 如果标题的空间是 9.4 厘米,我就写一个 9.4 厘米的标题。 每次都是 一页又一页。 何塞普经常给我发邮件,恳求我改变长度。 我一直在尝试,但在尝试的同时,我发现自己为了充实标题的内容而不断深入细节,这些额外的工作甚至在我写的时候我就知道会被删掉。 在《HMW》出版了几卷之后,我们才自然而然地开始改变标题的长度。
如果说在经历了每日、每周和每月的新闻报道之后,我曾期待写书的节奏会更加悠闲,那么很快我就想通了。 HMW 在 11 年内出版了 9 卷,对世界哺乳动物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每一卷都围绕一个大类编排,例如食肉动物、有蹄类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和蝙蝠,篇幅多达 1000 页,其中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全面介绍每一个已知物种。 一些大家族的文字和物种介绍单章就达 50 万字。 许多长篇专著的篇幅都比这个短。
还有图片,图片编辑何塞-路易斯-科佩特(José Luis Copete)精心整理了每卷的数百张照片,每张照片都由何塞普亲自批准。 将这些内容汇集在一起是 HMW 的另一项重大成就。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的最佳作品,也可以看到当地摄影师在难以到达的地方拍摄的稀有和分布范围受限物种的照片,他们的作品可能是首次出现在国际出版物上。
不管摄影师的声誉如何,或者照片库的专业性如何,所描绘的物种并不总是能被准确识别。 争分夺秒地为新照片或重新确定身份的照片撰写新的标题,让我想起了多年记者生涯中的一些趣事。 这是令人兴奋的,但也有额外的压力,那就是错误不会在后天被遗忘:它们将在机构图书馆的书架上留存几代人。
有时,大型图片库也帮不上忙,要找到一个物种的正确照片,甚至是唯一的照片,是一项需要坚持不懈的任务。 HMW8 几乎是带着一张古巴鼩鼱的照片付梓的,这显然是唯一可用的照片,直到出版前夕,不屈不挠的何塞-路易斯(José Luis)找到了这张极好的照片,照片上的鼩鼱在野外很少见。
孜孜不倦,耐心非凡。 作为字幕员,我的工作是提供文字描述所展示的物种,并解释它们在整个家族中的表现。 要诠释凝固在瞬间的姿势并非易事。 (正确的解剖学知识很有帮助。幸运的是,我们及时意识到,最初被描述为猖獗的雄性袋鼠的阴茎实际上是母袋鼠的尾巴)。 我向何塞-路易斯、编辑助理艾米-切尔纳斯基和安娜-科内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虚假的(大部分)到偶尔有用的,不一而足。 有一天,我盯着一页证明穿山甲尾巴尖悬挂在树枝上的图片看了半个多小时,然后给艾米发了一封紧急邮件,询问它是否可能是倒立的。 我猜想这件事早就解决了,但她还是向我表示了感谢。
先是在艾米的指导下,后来又在安娜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解 HMW 严谨的风格–对不起,是严谨;HMW 使用的是美式英语。 中年晚期的我已经开始为注意力不集中和思维不连贯而苦恼,偶尔还要背靠背编写 HMW 字幕、HBW 字幕(英语,但使用-ize 结尾和牛津单引号),以及为《鸟类生活》撰写新闻和特写(-ise 结尾;蔑视牛津单引号)。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分子方法在系统发育研究中的应用导致了所谓的分类学爆炸(尽管怀疑论者认为物种概念的爆炸导致了分类学膨胀)。 此外,还通过将大小、颜色或特征(如角的形状或尾长与体长的比例)的差异作为诊断依据来区分物种,这些差异以前被视为一个物种内部的差异。 从 2005 年到 2017 年 HMW7 出版,仅在 Murinae(真鼠和大鼠)亚科中就描述了 123 个种和 16 个新属。 目前,啮齿动物占所有已知哺乳动物物种的 40%,需要两卷 HMW 才能涵盖它们。
其他家庭也在进行类似的扩张。 例如,在牛科动物中,一种羚羊–开普蓝羚羊(Cape Blue Duiker)变成了 9 个物种,另一种羚羊–Klipspringer 分成了 11 个物种。 这个过程非常不稳定,以至于有时在编写 HMW 的相关章节时,会增加(或减少)物种。
分类爆炸给图片研究人员和无奈的标题撰写者带来了挑战。 在物种繁殖之前的图片库标签可能没有提供足够的位置细节来区分物种。 例如,现在这种适应沼泽的羚羊不再只有一种,而是有五种,每种都原产于非洲的一个主要湿地系统。 一个国家可能有不止一个物种(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两个、苏丹有两个、坦桑尼亚有两个),因此,仅以国家作为地点的旧标签不足以将它们区分开来。 由于诊断特征并不总是能在照片上很好地显示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实验室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看到这些特征,因此即使是描述新物种的权威人士也可能无法仅凭一张照片就有把握地识别它们。
当经常需要根据如此少的信息做出关键决定时,作者难免会时不时地改变对某项鉴定的看法,这就需要修改标题或撰写新的标题。 通常情况下,这些改动不会对出版计划造成太大影响,但有一位作者在一章的内容编排完成后等了大约九个月,直到该卷即将付印的前几天才告诉我们,九张图片中有两张被错误地识别了。 何塞-路易斯(José Luis)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图片研究工作,而我则在额外的压力下撰写了新的标题,因为我知道,这些标题将像记者所说的那样直接登载在版面上,而无需进一步的编辑干预。
分类学家在发现隐性物种并将它们从以前被视为单一广布物种的物种中分离出来方面做得很好。 据我判断,他们还善于为发现的物种提供适当的学名。 虽然我没有接受过古典教育,但我还是能认出许多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片段,这些名字都是由它们组合而成的:brevicaudus意为短尾,nigricollis意为黑颈,argentiventer(银+腹),等等。 在这里,我们将忽略白藜芦醇(Chiropotes albinasus)。 根据博物馆标本的描述,这种胡须崎猴被命名为 “白鼻猴”,后来发现它活着时鼻子是红色的。
遗憾的是,同样是分类学家,他们在命名常用名称时却缺乏想象力。 例如,根据 HMW9 中关于长指蝙蝠科(Miniopteridae)的章节,Shortridge 长指蝙蝠比小长指蝙蝠和小长指蝙蝠都要小。
此外还有大长指蝙蝠、大长指蝙蝠、比大长指蝙蝠小的大长指蝙蝠、小长指蝙蝠、比小长指蝙蝠和小长指蝙蝠大的最小长指蝙蝠以及中型长指蝙蝠。 哦,还有一只非洲长指蝙蝠,它是非洲发现的 12 种长指蝙蝠中的一种,但并不是分布最广的一种。 要在短短的标题中解释清楚这一切,同时又不失去读者的注意力,这又是一个挑战,我刚才可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数量惊人的蝙蝠物种被称为 “棕色……”,似乎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而不是所有已知蝙蝠中 99% 的特征。 不过,当新的哺乳动物被命名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真正的机智。 最近从普通剑鼻蝙蝠中分离出来的稀有且鲜为人知的分类群被称为非普通剑鼻蝙蝠。 (仔细想想就会明白)。
在其他蝙蝠家族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诗意的命名–雄辩的马蹄蝠、凶猛的喙蝠(让人联想到简-奥斯汀笔下愤怒的人物)、奇怪的大耳褐蝠–但这些称谓的原因从未得到解释。 我们不禁要问,”可疑的号耳蝙蝠 “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啮齿动物也是如此。 Rattus burrus惹恼了谁,才被冠以 “胡言乱语鼠 “之名? 布冯条纹草鼠比同属的许多其他物种更愚蠢吗?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科佩特达格松田鼠(Microtus paradoxus)又被称为矛盾田鼠。 哺乳动物命名中的悖论比比皆是。 马达加斯加有一种大短尾鼠,经检查,它比生活在同一座山的斜坡上的小短尾鼠要小。 不过,大老鼠的尾巴比小老鼠的尾巴长。 也许名字需要换一种读法,”大 “的是 “短尾”,而不是 “鼠”。
有些常用名称本身就是一首诗。 谁能抵挡绿河流域金芒刺地松鼠的诱惑? 我还喜欢这个物种,因为你只需要提到它两次,就已经有了大部分的标题。 (相反,我并没有从黄昏大蝙蝠那里获得太多的血统,它的学名Ia io 是所有生物中最简短的)。
有时,一个发现者的名字或地名与一个物种的突出特征结合在一起,会让人过目难忘。 谁会忘记伍斯南的宽头臭鼠或巴斯特的大脚鼠? 至少,HMW 称其为 Bastard 大脚鼠,因为它是以 Bastard 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在其他出版物上,它被称作 “杂种大脚鼠”,好像在给它取名字的时候,它咬了别人一口。
现代人倾向于避免使用普通名称来纪念那些无畏的博物学家,他们发现的物种可能是当地人非常熟悉的。 对于纪念伟大的自然学家或表彰实地工作者,或给予老伙伴一种不朽形式的名称,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义务为你做同样的事情。
无处不在的 “geoffroyi“来自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许多灵长类动物、蝙蝠和猫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用说鸟类和鱼类了。 马达加斯加还有一些物种被命名为grandidieri和petteri,以纪念其他法国博物学家(我们已经遇到过被称为bastardi 的法国马达加斯加专家)。 另一位对马达加斯加哺乳动物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的法国人阿尔方斯-米尔恩-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Edwards)的名字被简化为“爱德华兹”(edwardsi )(尽管他为一种雪柳和一种海螺起了两个名字)。 如果他活得再晚一点,他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全名alphonsemilneedwardsi,就像Akadon josemariarguedasi (阿奎达草鼠,2013 年描述)、Chiropodomys karlkoopmani (库普曼笔尾树鼠,2016 年描述)或Callicebus stephennashi (斯蒂芬-纳什的提提猴,2002 年描述)一样。 甚至还有一种老鼠属,以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馆长的名字Brucepattersonius 命名。 它们被简称为 “Brucies”。 而艾莉森-乔利(Alison Jolly)是一位狐猴专家,对马达加斯加动物群的保护非常有影响力,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鼠狐猴物种中,她的名字是简短的 “乔利”(jollyae)。
虽然我用两根手指就能数出从章节作者那里得到的赞美和感谢,但字幕组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一般都很融洽。 不过,有一两次,通常是当我不得不利用外部材料来编写字幕时,就会出现问题。
例如,一个属或科的所有成员可能都啃食类似的食物,如蚯蚓、草籽或块茎。 为了寻找新素材或新角度,连续六篇关于食物和喂养的文章,我需要翻阅作者引用的文献,有时甚至更多。 大多数作者对此都很从容,但有时我也会无意中卷入一场学术争斗。 为了填补空白,我翻阅了另一位专家的论文,也许是唯一的一位专家,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家族特别兴趣小组的主席。 当作者审阅字幕回来后,我从她的作品中摘录的每一句话都被重新写过,并附有 “这是一个老太太的故事 “之类的评论。 另一位作者在标题中加入了愤怒的质疑:”不是真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直到有人指出,每次的来源都是他与他人合著的一篇论文时,这些质疑声才渐渐平息。
大约 20 年前,我委托当地一位专门用被荷兰榆树病杀死的榆树木材制作家具的橱柜制造商为我制作一个书柜。 他的手艺很好,但可能不太爱读书,其中一个书架约有 13 英寸深。 多年来,我唯一占用这个空间的书籍是一对字典。 后来,我收到了我的供稿人赠送的《HMW》第一卷,它非常适合我。 目前,我有八卷《HMW》,另外还有四卷《HBW》,我也为它们提供了标题,当我收到第九卷,也是最后一卷《蝙蝠》时,书架就会满了。 这似乎是对我字幕组职业生涯的一个恰当总结。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委托别人再做一个书柜。
尼克-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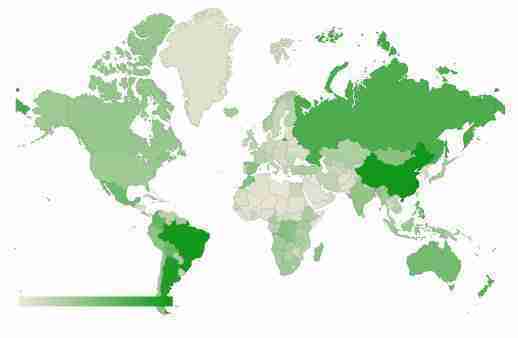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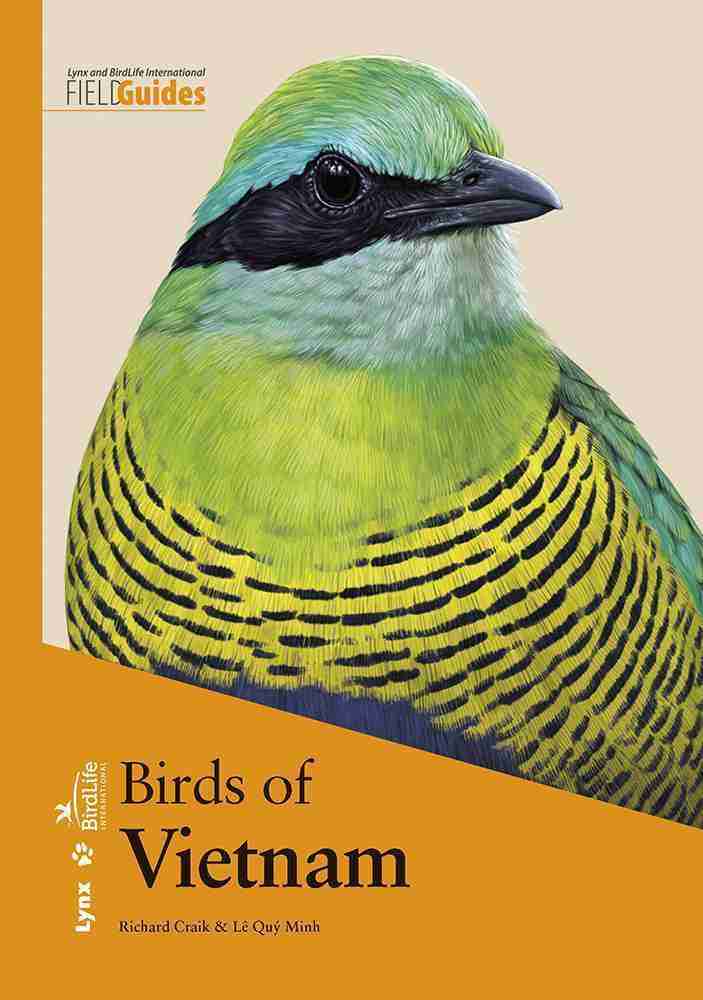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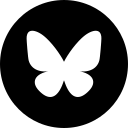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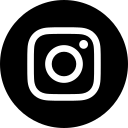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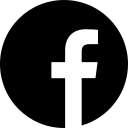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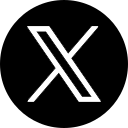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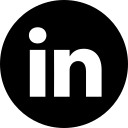



 版权 2025 © Lynx Nature Books
版权 2025 © Lynx Nature Books